
王世襄
本文原为与记者的对谈,为节省篇幅已删去记者的问话,并有所删节。
我出生于书香门第,长在京城的官宦之家。明代,先祖从江西
我父亲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。后来首都迁南京,北京日益萧条,他没有工作,有两所出租房租不出去,生活很窘迫。过去买的一些宋元瓷器和明青花都变卖了,借以生活。母亲也从此时得了高血压,和生活窘迫有关,五十多岁就去世了。不然的话,还可以多活几年,多画一些画。
我母亲的家位于江浙两省交界处的南浔小镇,濒临太湖,住有不少大户人家。金家就是其中之一,很富有。外公一直住在南浔镇,发家立业的是他的父亲,做蚕丝生意。外公没有出过国,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,办电灯厂,投资创办西医医院,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到英国留学。公元1900年,金家兄妹漂洋过海,前后历时五载。这在当时是少有的。公元1905年,他们学成归国后均各有成就。
大舅金北楼先生是非常有名的画家,他功力很深,山水、花鸟、人物无一不能,还创立了当时最重要的研习国画的组织“中国画学研究会”,学生很多,影响很大,还和日本交流画艺,是画界的领导人物。
我觉得北楼先生的花鸟已经开始有自己鲜明的面貌了,可是那些得意之作都留在家中,“文革”时全被人抄走了,到现在还没有露面。当时他是北方画坛的盟主,地位超过张大千,可是现在他的画的行市比较低,因为人们没有看到他的铭心之作。如果他活到八九十岁,一定有大成就。
我母亲也是当时女画家中的杰出者。字也写得好,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。幼年时和舅舅们一起在家馆学习。一天她父亲对老师说:男孩子读书写字,请您多加管教;女孩子早晚出嫁,不必太认真。我母亲听了很生气,认为不应该重男轻女,所以读书、写字、作诗词等特别用功。后来除大舅外,几个舅舅都不如她。
二舅金东溪,四舅金西都擅刻竹。尤其四舅搞了一辈子竹刻,被公认为近代第一家。
我有一个哥哥名王世容,比我大两岁。他聪明好学,又懂礼貌,亲朋都十分爱他。而我则顽皮淘气,不肯念书,到处惹祸,如上房、打狗、捅马蜂窝等,亲友都讨厌我。世容不幸十岁时病故,大家都说“可惜死了一个好的”。我母亲剩我一个,不免开始放纵溺爱。但有一个原则,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,有害身体的,则严加管教,绝对不许可。
我十岁时开始养鸽子,每天举大竿子撵鸽子,这对身体无害,可以准许我养。此后开始又养蛐蛐(蟋蟀),不仅花钱买,还结伴去郊外捕捉。出一身臭汗,晒得很黑,但步行多少里,也是个好锻炼,所以母亲也准许玩。此后又学武功,请老师教八卦和太极拳。我还拜清代遗老宫廷运动员学摔跤,他们都是有等级的“扑户”。从此身体特别好,在美国学校曾把美国同学手臂摔断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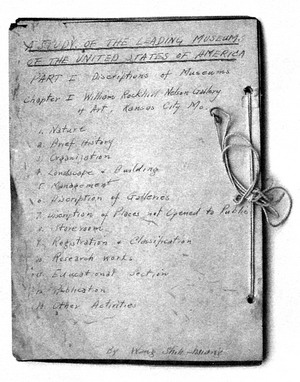 |
|
1948年王世襄考察美国、加拿大博物馆。此为调查手稿《甘泽滋城奈尔逊氏艺术馆》晒蓝本。 |
关于我当年的各种玩好,到七十多岁时我都写成专著或文章,不少读者可能已经看过。如未看过,不妨找书看看,我不愿也不可能再叙述一番。如再写一次刊登,未免有骗稿酬之嫌了。
我父亲曾出使墨西哥,回国后考虑到可能再派出国,所以把我送进美国学校,以便将来带我出国,可与外国学校接轨。这是一所专为美英侨民子女开办的中小学,学生全讲英语,只有少数中国学生。我在此从小学三年级上到高中毕业。英语不用学,听就听会了。1948年我去美国参观考察博物馆,人们都认为我是在美国长大的。可是英文我并未学好。英文好必须多看书,多写作,不用功不行,所以我的英文始终是低水平。每天下午回到家中,又请饱学的国学老师教我两个小时。直到1934年上大学才停止。老师十分认真,从国学基础课文字学、经史到诗词、骈文等都教。但除了诗词我比较喜欢,学到了一些以外,其他各门都没有用心去学,实在辜负了父母和老师,不过文言文还是勉强能写的。
1939年我母亲病逝,给我极大的震撼。深感玩了多少年,实在让父母伤心失望,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那年考上研究院国文系,仍住在园中,但所有的玩物都不要了,鸽子送朋友,狗成了看家狗,专心致志,上课读书,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转变。由于受家庭影响,也由于狂妄无知,第二年上报《中国画论研究》作为硕士论文题目。这是我最早写又是最难写的一本书,也是未写完已觉得不满意并有羞愧感的一本书。在园中一住又是三年,论文只写到宋末,获得了硕士学位。
20世纪50年代末,我父亲已去世。北京大学占用了燕京校园,需要办一个托儿所,和我联系购买此园,我同意卖给了北大,此后我再也没去看过。后来北大又将托儿所改为小学。完全出我意外,去年夏,小学校长来到我家,他说王家花园的松树已长大成林,十分幽美。又有一棵柽柳,通称三川柳,长得特别高大,北京市园林局定为受保护的珍贵名树。因此北大小学已成为北京极少数的园林式小学。
研究院毕业后,北京是沦陷区,一工作岂不成了汉奸。我仍住园中,准备利用燕大的图书馆,继续写完《画论》。不过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件后,美日宣战,燕京被日寇占领,我只好进城回家了。回家后,父亲说做事要善始善终,你在家好好地把《画论》写完。我又努力干了两年,全稿长达七十万言。但缺少自己的分析与评价,必须再用几年时间,修改一次,才能提高。所以长期束之高阁,不敢示人。直到八十岁后,一目失明,自知已无能力重写,又恰好有出版社愿为影印时,才得问世。
写完《画论》,此时我父亲已年迈,身边仅我一人,但他还是下决心要我离开北京,南下谋生。我经过成都,燕大复校,梅校长留我当助教。我不愿教书而未就。到重庆,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――是我父亲的老同学――同意我任秘书,因只能伏案写公文,不可能见到文物,学不到知识,故请求故宫复原时再参加工作。我很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,那里集中了多位大学问家,可以求教。请梁思成先生带我去见傅斯年先生,傅先生只问了一句话:“你是哪里毕业的?”我回答:“燕京大学。”他说:“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。”我只好告退。最后梁思成先生收容我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,名义是助理研究员,实际上是学徒。在学社我有机会阅读《营造法式》和清代匠作则例等,增加了我对传统家具的兴趣,对我后来的研究方向起了引导作用。
日寇投降后,我被派到北京清理追还战时损失的文物。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在平津地区为国家追回文物共六批,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。如加上从东京运回上海的善本书一百零七箱,数量当以万计。
文物是我经过调查侦察,会同国民党官方机构行政院院长驻北平办公处、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等,迫使对方交出文物,押送故宫,由故宫工作人员清点接收入库的。实际上我只有在点交时才看见文物,点交之后文物立即送故宫库房保管。我当时这样做,就是为了避免嫌疑。没想到还是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“三反”运动中,“打虎英雄”们只要调查一下档案,问一问写清单的故宫工作人员,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。但当时他们不调查,不分析,先锁定你是“贪污犯”。穷追猛打。
1947年初我从日本运回善本书后,立即去南京办理结束清理文物损失委员会职务事宜,就是为了尽快到故宫工作。约一年半后美国洛氏基金会赠给故宫一个名额,去美国、加拿大参观学习博物馆一年,当时只有我在语言上没有困难,所以马衡先生派我前往。1949年8月返京,即新中国成立前夕,我回到故宫工作,直到“三反”运动开始。至于解放后的故宫,由于总管全院事务的是党代表刘耀山,他本是农村私塾的一个老师,其水平可想而知。他不懂又固执,故一切工作很难开展。我写过两篇小文――《俄罗苏(sù)拍电影――砸瓷(词)儿》和《和西谛先生一夕谈》,读者会发现当时故宫的工作很难做,有意想不到的困难。
离开故宫,养病一年后,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。工作时间做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工作,业余时间则全部用在朱桂老(名启钤,号桂辛)交给我的任务上,为传世唯一的一本漆工专著《髹饰录》作解说。这是写完《画论》后我的第一部著作,并从此全力搜集、研究、编写不同文化领域的材料,一直到今天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二个大转变。因为故宫把我开除了,不能再为故宫工作了,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,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。《髹饰录解说》1958年完成,为了油印出版差点挨批斗,经过许多周折,受了许多气,到1983年才能排印出版,整整压了二十五年。当时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所处的最黑暗、最残酷的年代。因此我认为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,对知识分子真是恩同再造!
写完《髹饰录解说》之后,开始写古代家具,可惜不久便“文化大革命”,挨了多次批斗,只得半途而废。直到1985年才出第一本关于家具的书《明式家具珍赏》。这距开始搜集文献实物资料已有四十年之久,编入书中我个人所藏的明式家具也有八十件。
我收藏的家具后来都放在上海博物馆了。我当时是有不得不处理的原因。
北京实行私房改造时,凡出租房达到十五间,便要归公。我家有一所房长期出租,只有十一间,不够没收条件。房管局和街道知道我家中厢房存放家具,就全力动员我出租,并以如不出租,将占用厢房办托儿所或办街道食堂相威胁。不得已我只好出租,从此产权就不属于我了!家具只好堆入北屋三间。但后院有五家住户的小厨房利用我北屋的后墙作为厨房的后墙。小厨房都用油毡作顶,距北屋房檐只有三尺。任何一个小厨房起火,北屋和家具都将同付一炬。还有房管局安排搬来的住户,是白铁匠,整天打铁,焊洋铁壶,做烤箱,使我不能休息。他的老婆专捡破烂,堆了满院子,还在院内盖住房。我请街道协调此事,街道袒护他,因为我是摘帽“右派”。在上述情况下,我只有搬家了。但单位不分给我房,买房又买不起。恰好此时上博修建完工,有家具展室,但没有家具。香港朋友庄先生和我商量,想买我的家具捐赠给上博。我提出的条件是: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,自己一件也不能留,如同意,收入《珍赏》的家具我也一件不留,而且我不讲价钱,你给多少是多少,只要够我买房迁出就行。当时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,但我心安理得,认为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好去处。就这样,搜集了四十年的七十九件家具都进了上博。还有,七十九件中有明代四把一堂的牡丹纹紫檀大椅,是举世知名的最精品。在《珍赏》中只用了一件,出现过两次。按照我和庄先生的协议,我只需交出一把,可以自留三把,但我四把全交了。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,太难得了,我不愿拆散它们。还有在我家中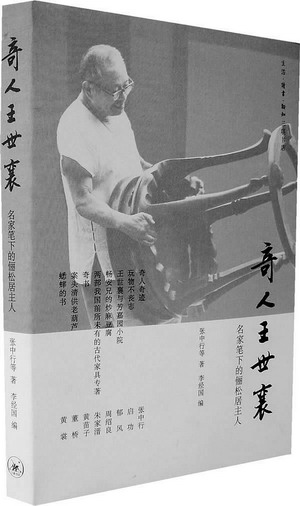 多年,四把椅子从未按应用的格式摆出来过。到上海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,那有多好啊!《珍赏》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,出书前我已送给了杨乃济先生,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。过了几年,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,我最近又无偿捐给了上博。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,共计八十件了。
多年,四把椅子从未按应用的格式摆出来过。到上海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,那有多好啊!《珍赏》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,出书前我已送给了杨乃济先生,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。过了几年,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,我最近又无偿捐给了上博。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,共计八十件了。
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“由我得之,由我遣之”的态度。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,就很满足了。遣送得所,问心无愧,便是圆满的结局。想永久保存,连皇帝都办不到,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!
我的《自珍集》的序中有以下几句话:
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,可能自寻短见,可能铤而走险,罪名同为“自绝于人民”,故万万不可。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,共同决定坚守自珍。自珍者,更加严以律己,规规矩矩、堂堂正正做人。唯仅此虽可独善其身,却无补于世,终将虚度此生。故更当平心静气,不亢不卑,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,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,全力以赴,不辞十倍之艰苦、辛劳,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。自信行之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,当可得到世人公正、正确之理解与承认。
半个多世纪,我编写出版了约四十种书,事实证明我就是按照上面所说的道路走过来的。
(摘自《奇人王世襄》,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,定价:37.00元)
